永远游荡和回归大地 | 荐书
- 时间:2018/3/2 新闻来源:热点快报网 阅读: 次
-

他发现、培养的“将军们”壮大成一支由几十位杰出作家组成的队伍,其中包括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欧内斯特·海明威和托马斯·沃尔夫
1944年4月,《纽约客》分两期连续刊登了文学编辑麦克斯韦尔·珀金斯的人物特写,不惜笔墨地给予了他本人长时间回避的荣誉。文章作者、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说,在当代文学领域,没有人像珀金斯那样,既非常重要又籍籍无名。
初入编辑行业时,珀金斯就曾表达过自己的志向——成为“坐在大将军肩头的小矮人,指导将军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无人察觉到这一点”。这个比喻巧妙暗示了他的一生,在他此后持续三十多年直至生命最后一天的工作中,他发现、培养的“将军们”壮大成一支由几十位杰出作家组成的队伍,其中包括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欧内斯特·海明威和托马斯·沃尔夫。
1947年珀金斯去世,他在生命最后阶段扶持的年轻作者詹姆斯·琼斯得到消息后一连数日不断想起由珀金斯编辑出版的《天使,望故乡》开篇的第一句话——“哎,失落的,被风凭吊的,魂兮归来!”正是这句话最初吸引琼斯从事写作。1951年詹姆斯·琼斯的小说《从这里到永恒》出版,这本当年在珀金斯的鼓励下艰难起步的作品获得巨大成功,最后一次证明了编辑的才华。
司各特·伯格是美国著名传记作家。1971年,刚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他开始为珀金斯的传记做研究工作,他发现这位与一个文学时代紧密相连的幕后人物既没人记录也没人评价,《纽约客》那篇名为《矢志不渝的朋友》的人物特写几乎是仅有的全面记录珀金斯生平的文章。
伯格花了七年从成千上万封书信、浩渺的书稿、一手的采访资料中梳理出一位“睿智、谦逊、低调、一丝不苟的正直”的形象,以“天才的编辑”为名写作、出版。
《天才的编辑》详细叙述了珀金斯如何发现一位又一位有潜力的作者,并帮助他们开启写作生涯。“他对待文学就像对待生死”,倚靠在那张堆满书稿、裂痕累累的办公桌上,“挽救可挽救的,栽培可栽培的,治愈可治愈的,保持美好的事物。”
书中相当大的篇幅集中在珀金斯与菲茨杰拉德、海明威和沃尔夫的交往上。作者将这些名头响亮的作家的天赋和成功用寥寥数笔带过,却把“天才的脆弱”暴露无疑。菲茨杰拉德二十四岁凭借《人间天堂》被视为“一代新人”的旗帜,之后竟长久困于年少成名的阴影,举步维艰;沃尔夫在《时间与河流》定稿之前,因为害怕与倾注了全部心血的作品告别,而强迫症似的无休止地修改;海明威的写作大胆鲁莽,容易过度修改、矫枉过正,《永别了,武器》中的某些部分他写过五十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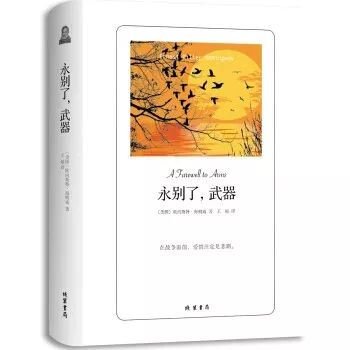
珀金斯之所以得到作者的信任和依赖,是因为他帮助他们走出泥淖,沃尔夫说是珀金斯为他创造了自由和希望。他曾在信中宽慰借酒浇愁的菲茨杰拉德:“每个从事文学的人都会时不时地厌倦生活。”他也曾鼓励年轻女作者南希·赫尔:“如果你认为你现在写得不好,那就对了,真正的小说家都是这么想的。据我所知,从来没有哪个人不是常常感到泄气,有些人甚至感到绝望,而我总是发现那是一种好兆头。”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漂亮的文字仰仗与生俱来的灵性,一流的作者从来不需要为遣词造句发愁。《天才的编辑》让我不幸发现,天才文学家也必得承受巨大的痛苦。这些诚实、残忍的记录类似一种祛魅,但是比起下笔如神、行云流水的想象,这样的故事更加真实感人。
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是珀金斯与他的作者之间的感情,作为敏感脆弱的灵魂他们互相依存,作为完美主义者他们又不得不互相折磨。《时间与河流》是珀金斯编辑生涯最耗心力的书。沃尔夫交出满满三大箱手稿,他对自己这些无节制的表达无能为力了。珀金斯从这堆书稿的最顶端开始改,理出详细提纲,修改意见细致到人物形象设定、对话和场景的穿插、背景材料的编排顺序……
珀金斯说“我认为汤姆(托马斯·沃尔夫)是个天才,我也喜爱他,不忍心看着他失败,对他的书我几乎跟他一样拼命。”《时间与河流》成为沃尔夫生涯中最伟大的作品,他把这本书题献给珀金斯——“一个无畏、坚定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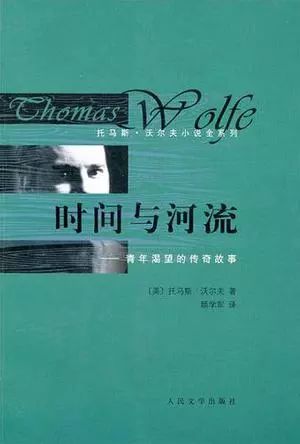
沃尔夫曾经和珀金斯讨论过一个写作计划,关于“永远游荡和回归大地”:永远的大地,是家,是心的归宿,一种让男人游荡的动力,让他们寻找,让他们孤独,让他们对自己的孤独又爱又恨。
1934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珀金斯和沃尔夫每天晚上八点半开始改稿,他们为每一处删改争论,之后各自伏案,直到深夜才走出办公室到露天酒吧喝一杯。我想,那些在夜空下散步的日子,对于珀金斯来说,应该既是寻找也是归宿。
